周国平在《灵魂只能独行》中曾写道,“一个人不甘心被世俗生活的浪潮推着走,而总是想为自己的生命确定一个具有恒久价值的目标,他便是一个有信仰生活的人。”庸人之争多有纷扰,智者却总能找到独自沉静的空间。这让我想到了离群索居,在暗默世界中谱出《命运交响曲》的贝多芬,更让我想到在瓦尔登湖畔搭起木屋的梭罗,用亲身实践写出了传世名作《瓦尔登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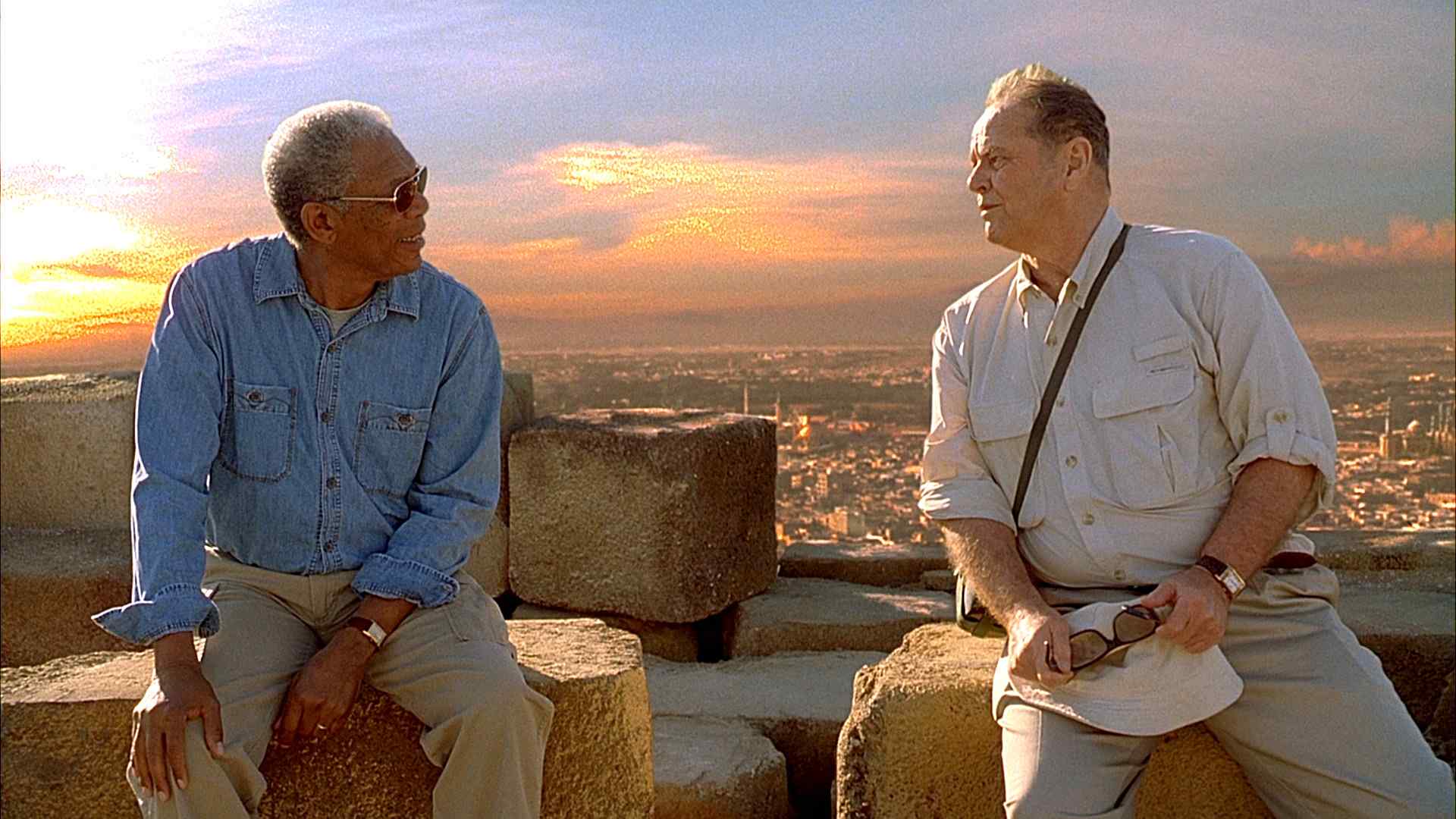
而梭罗写这本书的时候,才28岁。那一年,梭罗为了寻找人生意义,在家乡康科德镇瓦尔德湖畔,用借来的斧子在湖边盖了一个小木屋,隐居了两年。虽然这个地方才离家3公里,而且他的母亲还会时不时给他送饭,但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毫无理想追求又有些奇怪的人,却帮助了很多迷茫的人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让人读完后想问自己,人生的理想在哪里呢。
在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里,梭罗只有一张床,两张桌子和三把椅子。为了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梭罗开始学着用斧子开垦荒地,种植农作物、挖掘地窖、收拾屋子、烹饪食物,当然所有食物以素食为主。除了劳作,梭罗用剩下的时间观察自然,思考人生。清晨,他在湖中洗澡,白天在阳光下沐浴,黄昏在鸟兽的陪伴下沉思。他观察湖水,探索森林,识别各种鸟类的花纹,发现树木生长的规律。他在湖边散步,垂钓思考。他在小木屋里阅读写作思考,不与外界发生关系,拒绝现代文明的产物。他在这种极为纯朴的生活中获得了什么呢?
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可以说是大胆地批评了“消费主义”。书中曾提到,资本家们鼓吹消费,把各种非生活必需品和品味联系在一起,让消费者们相信购买奢侈品等于获得自己梦想的生活方式。劳动者们为资本家辛勤工作得到的报酬在手里转一圈,又在购买中流回资本家的口袋,人们就像工厂中的螺丝钉一样。“一种习以为常劫浑然不觉的绝望甚至在所谓人类的各种游戏和娱乐下深藏不辞。游而不戏,娱而不乐,因为工作比后只是绝望。”太多的物欲只会腐败人类的意志,侵蚀人的思想。换个角度思考,如果生活中只有必需品,会是什么样子呢?

在书中,梭罗写道,生活必需品只有四样,食物、住所、燃料、衣服,有了这几样东西且就能够满足人的正常生存和健康。而他自己的必需品则更少,一把刀、一柄斧、一把铲、一辆手推车就足够了,他靠这些工具建起小木屋,开垦农田;他的次要必需品是一盏灯、一些文具和几本书,他靠这些东西来滋养灵魂。在梭罗看来,金钱不是必需品。那什么是呢?人唯一的资本是时间,这是我们唯一拥有并能掌控的东西,所以应该以最简单经济的方式为生,然后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去体验生活,探索自己的精神世界。书里还有个特别有趣的地方,写梭罗观察自己的那些动物邻居,比如梭罗用了非常多的细节描写红色蚂蚁大战黑色蚂蚁,其中红蚁像个斗士一样锲而不舍,充满勇气,虽然最后因为实力差距太大,还是牺牲了。他也描写了其他的动物,有一开饭就过来捡食的老鼠,有一听到声音就咯咯藏起来的雏鸟,还有湖畔的水獭、浣熊、浅鸟,都仿佛是老朋友一般。书里写,“我常常在最深的积雪中,步行八里或者十里,专为了践约,去同一棵山玉榉一株黄杨或松鼠中的一个老相识去约会。”梭罗一方面肯定自然的造化神奇,认为众生平等,每个生灵都应该得到尊重,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有一种超脱的物质隐藏在自然世界之中,这股力量凌驾于自然世界之上。其实我们都知道人类对自然的态度曾有过非常大的转变。然而,无论人对于自然或是警惕或是轻视,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反复摇摆,自然对人类永远是平等的,并不会因为人类的态度而转变,也不会因为人类的价值观而动摇。书中写过令人感动的一幕,“夕阳同时落在富人和贫民院的窗上,而且同样灿烂,所有人门前的积雪,都一样在春天融化……我觉得,一个恬淡的人,生活在贫民院和生活在官殿里是一样的。”

梭罗在隐居的两年多时间里,不仅留下了瓦尔登湖,还写过多篇博物学论文,留下了一千多份植物压制样本,同时也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不论这些文献标本有多庞大,我们单单在《瓦尔登湖》这本书里就能看到一个极度充实的精神世界,而且这个精神世界我仿佛看到了陶渊明的身影。瓦尔登湖中,梭罗种土豆、种豆子,在劳动中审视内心,在简朴生活中得到宁静和快乐,如同陶渊明在空谷幽兰,这就是东方哲学的慎独和修身呀。
在书中,梭罗把在湖畔两年多的生活压缩成书中的一年,以春夏秋冬的轮回集中对比了生与死、新生与凋零,强调了死亡和重生的精神意义。无论是生死、美丑、矛盾,在他眼里没有非黑即白,没有二元对立,而是彼此转换、彼此相依,这种认知观更是道家哲学思想的核心。
年轻人的避世或许总带有一种愤怒,是一种现实满足不了心理预期的愤怒,而瓦尔登湖不是愤怒的,而是安宁和喜悦且富有生机的,“不管你的生活多么低贱,那也要而对它,好好过下去;别躲避它,也别给它起那么难听的名字。生活未必像你那么坏吧。”在湖畔居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后,梭罗离开瓦尔登湖重返城市,把他在瓦尔登湖湖畔的生活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虽然当时梭罗毅然决然的拿起斧子进入森林之中,如同老庄一样,但并不是为了避世,相反他的思想一直是积极入世的,他注重的是精神自由,而不是形式。一个人如果有着独立自由的人格,那么他住在哪儿,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其实并不重要。这种隐居的实验只是梭罗想尝试一种新的活法,就像他曾经说的,不希望自己临终时却发现从没有活过。
我们有时候不妨也问问自己,什么是幸福的生活,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听自己心里的声音,也许那份最纯真的理想即刻就会浮现,而当人有了更加高远的目标与理想,那么在他眼中就没有不可逾越的峰峦与沟壑,只需坚定地走向最远方闪耀光芒的灯塔,便能觅得生活最本真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