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一位天才作家出生在美丽的哥伦比亚海滨小镇阿拉卡塔卡,但出生后不久,便被寄养在外祖父家,外祖父天天给他倾诉往事,外祖母则给他讲了非常多的印第安神话故事,也正是这段童年经历,这位天才作家早早就体会到了孤独,也在他的心里埋下了想象与魔幻的种子。1947年,他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律,意外尝试下开始了创作之路。1948年,因哥伦比亚内战爆发,他只能转入卡塔赫纳大学攻读新闻系,不久开始了他漫长的记者生涯,也正是这段人生经历,内心的敏感为他之后的文学创作打下来基础。1967年,他创作的《百年孤独》惊艳世界文坛,并于1982年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位天才作家便是加西亚·马尔克斯。

塞涅卡在《致鲁西流书信集》中曾写道“如果你想从阅读中获得值得你永远铭记在心的知识,你就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研读那些无疑是富有天才的作家们的作品,不断从他们那里取得养料”。那《百年孤独》无疑就是天才作家下的作品,它的“魔幻现实”在于随着你人生的经历不同,会看出不同的东西。
而这本书的写作技巧更是影响了很多作家,比如《百年孤独》开头那句非常著名的话,“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就被后来很多作家借鉴过,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伊莎贝尔·阿连德的《幽灵之家》、莫言的《檀香刑》等等。这种写作手法在当时很巧妙,让读者一上来就感觉相当不简单,他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疑问,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是谁?为什么多年后他会面对行刑队?又为什么他会回想起看冰块的时候呢?而这种极富创造、教科书般的写作技巧在这本书里还有很多很多。
《百年孤独》如果用简单的话来概述的话,讲的是位于拉美地区的虚构小镇马孔多中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整整100年的兴衰史,这也是书名《百年孤独》的由来。
小说从布恩迪亚家族的第一代人物——丈夫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与妻子乌尔苏拉开始讲起,丈夫带着妻子以及一批年轻人从旧市镇中出走,在一片荒野上建立起了新的小镇——马孔多,这不仅是故事的开端,也是布恩迪亚家族百年悲剧的序幕。
随后,马孔多吸引到了一伙流浪民族吉普赛人,其中一位名叫梅尔基亚德斯的吉普赛炼金术师尤其智慧,他给马孔多人带来了许多从未见过的欧洲新奇事物,如冰块、望远镜、放大镜等等,这也激起了丈夫何塞对科学研究的浓厚兴趣。
后来,马孔多日渐繁荣,但夫妻二人心中却始终笼罩着一层阴霾。因为他们实际是近亲结婚的表兄妹,因为害怕生下长猪尾巴的畸形婴儿,两人一度不敢同房。最终他们发现担心是多余的,他们一生总共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而且都没有畸形。
布恩迪亚家族也由此迎来了第二代人。而从这一刻起,小说才真正展现出其魔幻现实主义的本质,一切都开始魔幻了起来。
不知为何,一种奇怪的失眠症蔓延到了整个马孔多,所有人都变得不再需要睡觉,也逐渐变得健忘。他们甚至开始忘记日常用品的名称和用途,幸运的是,神秘的炼金术师梅尔基亚德斯再次来到了马孔多,用一种特殊的药水帮助了人们治愈了失眠症,并在临终前,给布恩迪亚家族留下了一间炼金术研究室和一卷难懂的羊皮卷。在炼金术师梅尔基亚德斯死后,丈夫何塞逐渐沉迷于炼金术,并因此精神失常,他的妻子只能无奈的把他绑在院子里的大栗树下。至此,第一代布恩迪亚家族的男人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百年孤独》故事的重心也由此转移到第二代人身上。
在第二代人中,次子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是小说中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人物,也是贯穿全书的灵魂角色。在他刚成年不久的时候,马孔多所在的国家爆发了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战争,战火波及到了新兴的马孔多小镇。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毅然选择离开家乡马孔多,参军入伍,选择为自由派而战,并由此开启了他传奇的一生。
书中用了一段非常经典的文字来描述他的一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发动过三十二场武装起义,无一成功。他与十七个女人生下了十七个儿子,一夜之间都被逐个除掉,其中最年长的不到三十五岁。他逃过十四次暗杀、七十三次伏击和一次枪决。”在这场延绵多年的国内战争中,奥雷里亚诺上校一度成为自由派的军政领袖,主导着整个战争。但也使他逐渐变得冷酷无情,与家人生疏。后来,他对战争感到了厌倦,不知道自己做这一切的意义何在。最终,他强制要求自由派与保守派进行谈和,结束了战争,回到了家乡马孔多并孤独的度过了晚年。
而马孔多这座小镇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浩劫中经历了无数动荡,在不间断的流血事件中见证了两个阵营表面上的大义凛然,实则上却是各自为利的荒谬战争。
战争过后,百废待兴的马孔多迎来了一个命运的转折点。
一个美国商人在马孔多发现了当地盛产的一种新型水果——香蕉,他从中看到了商机,并迅速组建了一家香蕉公司,把这种新型水果出口到美国和欧洲,赚的盆满钵满。由于香蕉产业的快速发展,马孔多迎来了极大的繁荣,铁路、路灯等各种现代化设施来到了马孔多,而大量外国人的涌入使马孔多变成了一个大型城镇,但原住民们也不得不接受自己因此被美国人所统治的现实。

而布恩迪亚家族也在此时繁衍到了第四代人,这时最主要的人物是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拉美文化里,如果家族里出现了重名者,会用数字区分),香蕉公司带来的巨大利益让许多马孔多原住民都成为了公司的工人,其中就包括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由于香蕉公司工作条件恶劣,这引起了工人们的强烈不满,何塞·阿尔卡蒂奥作为工会领袖组织工人们进行游行示威。然而,香蕉公司的高层竟勾结军官,下令对罢工的3000名工人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而何塞·阿尔卡蒂奥蒂第二是这次屠杀中唯唯一侥幸存活下来的人,政府和公司合谋掩盖了屠杀的真相,他成了唯一的一个知情人。为了躲避政府的抓捕,他躲在了数十年前的吉普赛人炼金术师梅尔基亚德斯留下的研究室里,并开始研究梅尔基亚德斯留下的羊皮卷,却终其一生都未能解开其中的奥秘。
之后,马孔多经历了怪异的持续4年11个月零两天的暴雨,这场暴雨摧毁了香蕉公司带来的所有繁荣,马孔多又再次回到了原始荒凉的小村庄状态,人口也几近凋零。
而故事也将迎来尾声。
此时,布恩迪亚家族来到了第六代人,这时整个家族只剩下最后一个男性奥雷里亚诺和最后一个女性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奥雷里亚诺的姨妈)。奥雷里亚诺深受炼金术师梅尔基亚德斯留下的羊皮卷吸引,废寝忘食的寻找着破译的方法。而常年在外国的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因为机缘巧合回到了马孔多,但两人都不知道对方与自己有血缘关系,受到布恩迪亚家族血脉的感染,家族最后的两人疯狂的爱上了对方,最终竟然如第一代布恩迪亚夫妻所担心的那样,因为乱伦而生下了一个长着猪尾巴的畸形婴儿。阿玛兰姐·乌尔苏拉也因产后失血过多而死去。奥雷里亚诺只得一人照顾这个婴儿,在第二天早上,他发现他的孩子被蚂蚁啃食殆尽,只剩下了一张皮正在被蚂蚁搬运回巢穴。
在这一刻,奥雷里亚诺脑海中终于看懂了梅尔基亚德斯留下的羊皮卷。他的第一句话是,“家族的第一个人被困在树上,最后一个人正被蚂蚁吃掉”,他疯了一般冲到了放着羊皮卷的研究室,甚至忘掉了刚刚死去的妻子和孩子,如饥似渴一般破解着羊皮卷。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能够完全看懂这份百年前吉卜赛人留下的手稿。
原来,这是一部记载布恩迪亚家族百年历史的预言书。
在这羊皮卷中,他得知了家族百年的历史,得知了自己的身份,也得知了自己的妻子原来是自己的姨妈。正当他准备看看记载着自己未来命运的最后一页时,他突然意识到这一切已没有意义。屋外狂风呼啸,一股猛烈的飓风席卷了整个马孔多,而整个小镇和镇上的人们一同从这个世界上被抹去了。

“这座镜子之城——或蜃景之城——将在奥雷里亚诺·巴比伦全部译出羊皮卷之时被飓风抹去,从世人记忆中根除,羊皮卷上所记载一切自永远至永远不会再重复,因为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这便是全书的最后一段话,故事就到此结束了。每次读到这个结局的时候,真的有一种被震撼到的感觉,尤其是全书那最后一段话,作者只用寥寥几句话就写出了整个家族百年命运的终局。那句“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带来了一种扑面而来的肃杀气息,简练而又不容置疑,仿佛是来自于上帝的审判。
从结局来看,《百年孤独》是一部非常典型的打破第四面墙的作品,不仅全书讲述的是布恩迪亚家族的百年兴衰,而书中炼金术师梅尔基亚德斯留下的羊皮卷也是讲述布恩迪亚家族百年兴衰的预言书。在故事中,羊皮卷被作者提及了很多次,不少家族的成员试图去破解它,但都没有成功。而在读的过程中,也从未猜想过这个不起眼的羊皮卷是整个故事结局最大的伏笔。而这羊皮卷的预言本质就是马尔克斯精心设计的“元叙事”陷阱,当奥雷里亚诺破译出“马孔多将被飓风抹去”时,读者手中的《百年孤独》也恰好翻至末页。这种“书中书”结构,似乎模糊了虚构与现实的边界。正如博尔赫斯在《小径分叉的花园》中写道的“小说包括宇宙”,马尔克斯让羊皮卷成为了一面镜子,照出读者自身正在阅读布恩迪亚家族命运的荒诞感,确实很高明。
而书中最为复杂的应该是书中人物的行为动因,比如全书的灵魂人物奥雷里亚诺上校,小说中详细描述了上校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经历,但在关键的地方都是含糊其辞的,比如上校为什么突然决定从戎入伍为自由派作战,哪怕他甚至并不清楚自由派的纲领?为什么上校会突然厌倦战争,甚至不惜背负胆小鬼的骂名,草草结束内战?又为什么他晚年要独自躲在炼金房中,一遍一遍的重复制作小金鱼,又一遍一遍的把做好的小金鱼熔掉。这些问题作者马尔克斯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语句阐明为什么,只是通过故事透露出了一种魔幻的、难以言说的神秘感,来让读者从感性上体会到书中人物行为诡异的原因。不仅是上校这些难以解释的行为,书中还有许多常人觉得难以理解的行动,但很奇怪的是,虽然我们在理性上觉得这简直不可理解,但是我们又会在读的过程中感受到一股内在的和谐统一感,仿佛在他们世界中做这样的事情是再正常不过的。为什么呢?促使奥雷里亚诺上校以及其他人物做这么多难以解释的事情的动因到底是什么呢?这个谜底其实一直就在谜面上,这本小说从一开始就把答案告诉了我们,这种奇怪诞又和谐统一的神秘感的真实身份正是他的书名——“孤独”,对孤独感由内而外的、仿佛细致到每根头发丝般的描绘,就是这本书最大的魅力,也是它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被全世界读者们疯狂追捧的主要原因。
一、不可逃脱的孤独
什么是孤独呢?
很多人对孤独的感受都会不同,大部分人对孤独的理解是我没有朋友、没有能陪伴、懂我的人或者没有社交生活等等,但这只是孤独的表象具现。而在哲学上,孤独的根源首先是我们这个主体对我们主体生命存在的清晰认知和把握,这让我们能够清晰的明白自己这个主体与外界他人的客体之间的界限和疏离感。
可能比较难以理解,换句话讲,就是现代人吃饱了喝足了,对精神的追求越发的关注了。人类在这个阶段会清晰的意识到自己是独立的个体,也意识到自己与他人有不同的精神追求。这种区别意识让我们不可避免的开始与枯燥的他人疏离,也因此当我们越是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独立的,越是追求自由和独立思想,这种与他者之间的界限和疏离感就会越强烈,我们就会越清晰的感受到孤独。或者更具体点说,就是自己这独一无二的存在而感到焦虑、苦闷和空虚。但这是扎根于我们存在之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孤独成为了现代人的固有属性,也是我们每个人乃至人类文明必须面对、无法逃脱的命运。
正因如此,《百年孤独》这部小说才有这么大的价值,因为它堪称是人类孤独的百科全书,它在给我们展示各种各样不同的孤独感的同时,也带给我们思考,我们究竟该如何去面对命运中不可逃脱的孤独感呢?
二、无爱的孤独
首先,《百年孤独》中最普遍存在的孤独是无爱的孤独。
在故事的结尾,最后一代奥雷里亚诺和他姨妈生下猪尾巴的畸形婴儿之后,作者马尔克斯在文中戏谑的评价道,“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第一个在爱情中孕育的生命”。这句话也同时在向读者揭示,布恩迪亚家族在百年中都未曾有过真正诞生于爱情的生命。事实也确实如此,除了第一代的妻子乌尔苏拉之外,布恩迪亚家族百年来的所有成员都像是冷漠的机器,每个人之间都隔着一堵厚厚的墙,把彼此彻底隔离。夫妻之间有情欲,有共同的利益关系,却鲜有爱情。兄弟之间只有那可怜的共犯情感,其余时间都像是陌路人,谁也不关心谁,谁也不在乎谁的死活。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爱的世界里,彼此感受着情感上的孤独。
在现实生活中,当然这样极端的例子是少数的,但是作为一种极端化的艺术展现方式,布恩迪亚家族的情感疏离其实更隐喻了作者马尔克斯对于爱与孤独的深刻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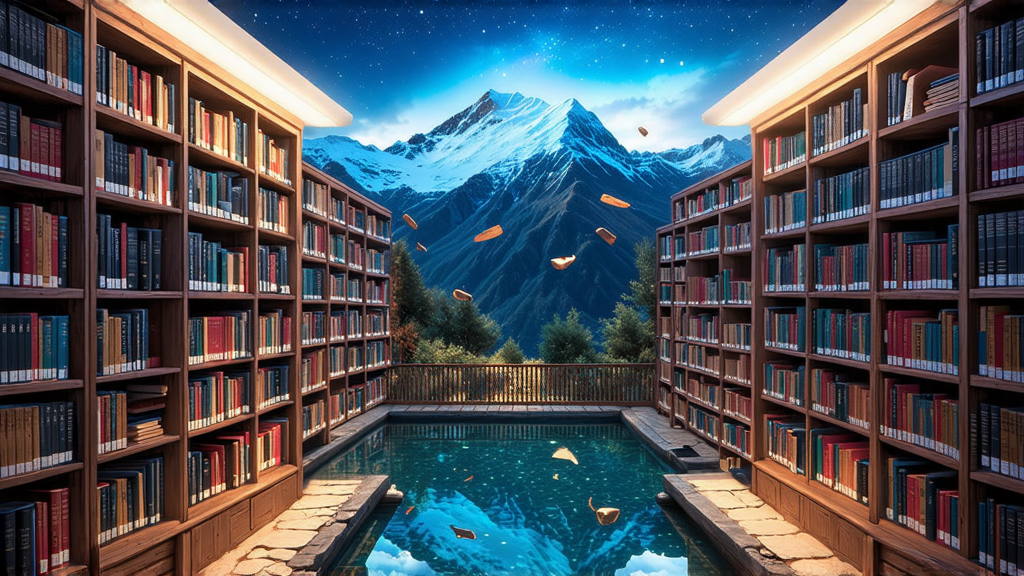
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曾写道,“没有爱,人类一天也不可能存在”,这仿佛验证了布恩迪亚家族的命运,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曾写道,“世界上只有一种地狱,那就是再也不能去爱”,也仿佛预言了马孔多小镇的结局——但丁笔下“冰封地狱”。
马尔克斯无疑也认可爱的重要性,所以他煞费苦心的为马孔多的布恩迪亚家族安排了最终的大结局,在羊皮卷的预言下,马孔多被飓风从地上彻底的抹去。这样的结局形式表面上是对《圣经》中索多玛和蛾摩拉神罚叙事的复刻,但若深入拉美历史的褶皱,这一结局也无意是刺向殖民暴力那段历史的匕首。马孔多的飓风是“被扭曲的爱”对本土文明的终极报复——当爱沦为权利与欲望的遮羞布(比如美国人的香蕉公司以“开发”之名掠夺拉美),其反噬必然以文明的湮灭为代价。马尔克斯的宿命论并非是对神权的屈服,而是对拉美那段“失语史”的悲愤重构。
所以,我们再来看那羊皮卷就能理解它的含义了,它的本质上就是对殖民者的判决书——拉丁文(殖民者的语言)写成的羊皮卷,以“科学理性”之名(炼金术师梅尔基亚德斯隐喻着欧洲启蒙者)宣判马孔多的死亡。这正是拉美百年命运的缩影,本土文明在“被书写”中失去了自我阐释的权利,最终成为他者叙事的一道注脚。
这难道不孤独么?这难道不让人悲痛么?
从个体上升到文明的孤独,这无疑是深刻的。
那句“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既是上帝对索多玛的裁决,也是马尔克斯对拉美未来的绝望警示:若不能打破“无爱”的循环,文明的重生终将是一场虚妄。
三、存在本身的孤独
而百年孤独中第二层孤独,是存在本身的孤独。
在书中,奥雷里亚诺上校是我非常喜欢的角色,他从小就一直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他遇到机会就毅然投身到了两派的内战,试图用战争排解自己的孤独。而到了晚年,他幡然醒悟,认清了自己多年来的奋斗只是为了排解孤独这个事实,他也因此变得更加孤独和否定自己的存在,只能一遍又一遍的把自己做好的小金鱼融掉,循环往复,以这种重复的创作来缓解孤独感。而上校的妹妹——终身不婚的阿玛兰妲,在老年也一直饱受存在带来的孤独的折磨。她早早就开始缝制自己的裹尸布,缝好了又拆,拆好又缝,期待早日死去,抹除自己的存在。而最后一代的奥雷里亚诺甚至是一个连自己是谁生的都不知道的私生子,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从小就发疯一般投身到羊皮卷的解读当中,以此来缓解孤独。这样的人物在故事中还有很多很多,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很苦恼于自己的存在,他们搞不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自己必须要忍受这种存在带来的孤独,因此只能投身于无意义的消磨时光当中去,以此来排解孤独。
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过去的一切宗教神秘都被祛魅了。人类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不需要依托于神的存在而存在,我们的存在就是本质,不需要外界的力量给我们赋予意义,但同时我们也开始苦恼。
既然如此,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存在?
我们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呢?

有人会说,你的人生掌握在自己手里,你的人生意义需要你自己去发掘,自己去赋予。这听起来很好,很自由,但现实情况是人类很多时候其实并不像自己想象中那么渴望得到自由,因为自由往往意味着责任,意味着无可逃脱的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的义务。但人性是既想要自由,又不想负责任,因为选择的责任是重大的,因为自己的人生赋予意义是困难的。
作者马尔克斯在一次访谈中说到,马孔多与其说是一个地方,不如说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或许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一种面对不可理喻命运的困惑感和虚无感,以及沉迷于自己世界不被他人理解的自我隔离。面对困惑和虚无,他们采取了自我隔离的方式,把自己隔离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以此来获得一种宁静和自足,来反抗不可理喻的命运。可以说,孤独既是他们可悲的状况,也是一种自我拯救的方式。上校循环往复的做小金鱼,阿玛兰妲重复做自己的裹尸布,都是拯救的体现。
有人说,这种所谓的反抗和拯救有点太过消极了,并不能真正改变什么。但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在面对荒诞与虚无时,如何找到生存的意义本身就是一场内心的革命。外在的变化未必能及时到来,而内在的拯救却能直接关系到个体是否能以尊严和自由面对命运,上校和阿玛兰妲虽然无法扭转自身的命运,但他们通过自己的方式,与孤独、虚无、命运进行了最真实的对话,这本身就是一种意义深远的反抗。
四、超越孤独
我想起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与奥雷里亚诺上校晚年熔铸小金鱼的行为仿佛就是镜像对照,二者皆是用“重复”对抗虚无。但有所不同的是西西弗斯的重复是自我确证(推石上山),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接受它。而上校的重复(或者说创造)是自我消解(将金鱼熔毁),在孤独中与命运不断对话,寻找自我和存在的意义。上校的这种“无用”的重复仿佛就是萨特在《存在与虚无》那句“人是一种无用的激情”的注解 ——
他清醒的意识到行为的无意义,却仍以坚持与努力的姿态完成对荒诞命运的嘲讽。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上校和西西弗斯虽然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但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两种做法,互相之间似乎构成了彼此的反面。
那么这两种做法究竟哪个更正确呢?
我想人生是没有唯一答案的,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同。因为每个人的经历各不相同,我们只能在未来的道路上自行判断。
我特别赞同森博嗣在《孤独的价值》的观点 —— 孤独是美的,是有生产力和创造力的。人之所以是一种高级动物,正是因为人有感受孤独的能力,并且能在孤独中去创造。虽然萨特告诉我们存在的荒谬和无意义,但“无用的激情”是我们对抗孤独的力量,通过“激情”追寻精神上的创造,通过写作、艺术、音乐、爱情等等形式,我们努力在无意义的世界中找到自我价值和存在的理由。尽管这种“激情”无法改变生命的运动景象就是自我消亡的结局,但却能够为个体提供对抗虚无的力量与内心的慰藉。
当马孔多的飓风在当代精神荒原上盘旋,那些被熔毁又重铸的小金鱼已化作星火,闪烁在人类文明的褶皱中。从奥雷里亚诺上校的熔炉到萨特笔下咖啡馆里握笔颤抖的手,从加缪笔下滚落山崖的巨石到梵高画布上晕开的颜料,这场对抗从未改变本质 ——
我们依然在用创造对抗消亡,明知徒劳的激情依旧是我们对抗存在虚无的武器。当推石者开始在山巅雕刻花纹,当荒诞的命运成为创作的画布,永恒轮回的诅咒便裂开一道缝隙,透出人类精神最璀璨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