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这句耳熟能详的经典台词,出自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般被译为“生存还是毁灭,那是一个问题”。这种翻译方式似乎已经约定俗成,但这只是一种文学上的转译。从哲学的角度来看,to be 被翻译为“存在”更为妥当。而在汉语中的“是”、“在”、“存在”都难以涵盖英语中 be (德语是 sein )的全部意义。对 being/sein 的追问,被西方哲学看作所有一切问题的根本。

纵观西方哲学史,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其代表作《存在与时间》中对“存在”问题的发问,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我特别喜欢其中一段话:“常人到处都在场,但却是这样:凡是此在挺身而出来决断之处,常人却也总已经溜走了。然而因为常人预定了一切判断与决定,他就从每一个此在身上把责任拿走了”,如果要把哲学风格类比为音乐流派,康德是一名伟大的巴洛克音乐家,尼采是一名重金属摇滚的主唱,黑格尔则是一名伟大的交响乐作曲家,那么海德歌尔绝对是电子音乐中的新世纪之王。
闻一多先生也说过“书要读懂,先求不懂”,其实与艾德勒在《如何阅读一本书》里一句话很像,“第一次阅读一本难读的书时,不要企图了解每一个字句”,而这本 1927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绝对是每一位哲学爱好者最难读、或许是必须会去挑战的哲学著作之一,这倒不是因为海德格尔的思想有多么天马行空,而是因为他创造了很多词语的全新用法。所以有人说,海德格尔写的都是诗,而不是传统的哲学。
《存在与时间》的开篇就直述根本目的,就是讨论存在的意义。“存在”的德语是 Sein,是中性的,加上冠词就是 das Sein。“存在”的英文是 being,也就是动词 be 的名词化形式。中国学者在翻译《存在与时间》的时候,因为汉语中不存在 Sein 和 being 的对应词,提出了很多完全不一样的翻译。有人认为存在应该翻译为“是”,有人认为应该翻译为“在”。英语中be在具体使用时,根据时态和人称会有各种变化,而在中文里,“是”后边一定要接一个词,例如“我是王某某”等。也就是说,在语法上,中文里的“是”只能做系动词,而英语和德语里的 be 和 sein 可以单独做谓语。“ I am ”之后可以不加任何词,就表示“我是”或者“我存在”。西方人发现,不论主语和宾语怎么变,“ be ”这个词一直都出现在那里。这个“是”或者“存在”意味着什么?在西方哲学的历史中,所谓的本体论的终极问题就是在讨论这个“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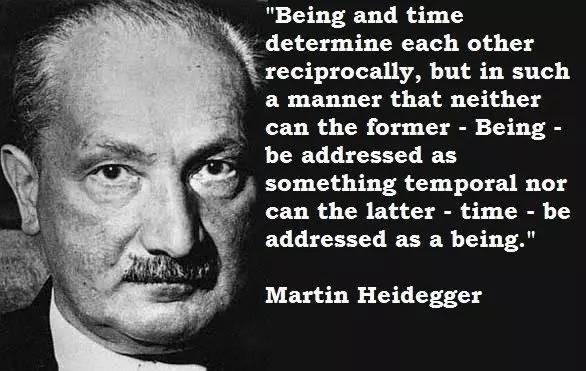
在西方历史上有不少哲学家讨论过存在问题。但是,海德格尔从一开始就和别人的谈法很不一样。他总结了三种以往对存在问题的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但这也意味着,存在是哲学史上讨论最不清楚的概念;第二种看法认为存在是无法定义的;第三种看法认为存在是自明的概念,因为在进行任何讨论的时候都要涉及存在的概念,所以就不用对它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了。
海德格尔则对“存在”( Sein )和“存在者”( das Seinende )作了重要的区分。人们每天都会接触很多特殊的存在者,如一只杯子、一辆车、一棵树、一片云等,但是存在本身并不只是某一类的抽象的共性,也不是存在者的一种属性,存在本身不是任何特殊的存在者。由此,对存在的讨论仿佛陷入了一种困境:一方面不能离开存在者来谈存在;另一方面,如果从任何具体的存在者来谈存在,都没法彻底地把握存在。所以,海德格尔的思路就是以人这种特殊的存在者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谈存在。在《存在与时间》里,海德格尔把人称为“此在”,德语是 Dasein。“ Da ”在德语里是一个很常用的词,意思是那里或者再那里,“ Dasein ”就是在那里的存在。
为什么要以人-也就是此在-作为切入点来谈存在呢?海德格尔认为,人不同于其他任何存在者,人对存在是有所领悟的。换句话说,人是在他自己的存在中和存在本身打交道的。人恰恰是因为对存在有所领悟才成为了人,人才得以存在。与动物不同,人的特殊性在于,人会追问存在,也就是提出关于存在的问题。所以海德格尔说,人这个存在者可以在自身的存在中显示自己。现代人的根本问题就在于遗忘了存在。人们只会研究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存在者,研究他们运动的模式和具体的样态,却忘了背后真正的基础,也就是存在本身。哈姆雷特提出的对存在的终极追问,也很少出现在人们日常的思考 之中。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此在”做出了根本规定,那就是“在世存在”。晚年的海德格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思想的事业来自“在世存在”这个简单的事实。“在世存在”的德语是In-der-welt-sein,按照字面意思解释就是在世界中的存在。海德格尔认为,人生活在世界上-就是这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支配着一切存在者的意义。 海德格尔创造了很多新词汇来代替传统哲学中的概念,用来更贴切地传达自己的哲学思想。例如,他不用“主体”来指代人,也没有将“人”与“意识”拆分开来,而是用此在( Dasein )一词将人与存在和对存在的意识牢牢捆绑在了一起。值得注意的是,“此在”不是固定的,也不是已经完成了的,而是有待实现的。“有待实现”在德语中是 zu sein ,也就是哈姆雷特的灵魂拷问“ tobe ”。海德格尔还说,人不仅存在而且不得不存在,“此在”被赋予了存在的使命。这就是人的生存( Existenz)。“ Existenz ”一词的词源意思是“站出来”,体会一下,是不是蕴含了一种人不得不直面存在的勇气呢?人不得不存在,也就不得不为自己的存在做出一系列的选择,为自己的选择承担一系列的责任与后果。用海德格尔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此在”总是作为它的可能性而存在。人在诸多的抉择之中实现了诸多的可能。“此在”进行选择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实现其本真状态( Eigentlickheit )。概括地说,本真就是忠于自己,成为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海德格尔认为,只有本真的此在才是真正的此在。另一种结果就是人服从预先给予自己的选择,这样就实现了他的非本真性 ( Uneigentlichkeit )。非本真性的结果就是“常人”( das Man ),这颇有《伤仲永》里所说的“泯然众人矣”的感觉。常人是没有个性的,大家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因此“常人”是没有面目的、人云亦云的、随波逐流的。
“此在”是被抛进世界的。这是一种非常生动的表述。“被抛”并不是指被遗弃,而是强调一种“身不由己”。被抛的物体的初始状态并不由自身决定,而人的存在之于人而言也是一种“身不由己”。“被抛”意味着人的出生是不由得自己选择的。人们从来没有机会主动选择自己的父母、家庭、先天的身体条件,但是如何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可以有所选择的。海德格尔用筹划(Entwurf)一词来表示“此在”能够主动地应对自己的处境。“被抛”与“筹划”和“本真”与“非本真”之间是有关联的。海德格尔把非本真的存在称为“沉沦”(Verfall)。沉沦有两重含义:第一,“此在”将自己理解为具有一定性质的实体;第二,“此在”进入了一个公众的世界,而不是一个自己的、私人的世界。在第一重意义上的“沉沦”强调的是作为个体的人自我束缚,画地为牢。在第二重意义上,人作为“群居动物”如果不能保有一个私人的世界,如果不能明确地知道自己欲求什么,厌恶什么,想成就什么,就会沉溺于闲谈、好奇和两可(得过且过)之中。
海德格尔说,此在是先于自身的。这意味着“此在”时刻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然而,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中,有一种终极的可能性就是死亡。死亡就是一把随时可能掉下来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结一切的可能。所以,在《存在与时间》里,海德格尔把死亡叫作一种“悬欠”状态,所有人都欠着一死。虽然万事万物的寿数都有一定的时限,但是只有人类明白死亡的意义,人类也就永远处在对死亡的焦虑、恐惧之中。海德格尔有时并不直接使用死亡这个词,而更多地使用虚无(德 语是Nichts,即英语的nothing)。相比起“死亡”这一必然的事实,海德格尔更关心的是“此在”对于“死亡”这一可能性的理解。
人们是如此地害怕生命的终结,然而没有死亡,生活也将失去意义。人们对生活的所有理解,人们对自身行动的每一项抉择,难道不都是建立在“终有一死”的前提之上的吗?如果人能够永垂不朽,有无穷无尽的时间做想要做的事情,也就不存在心愿、期许、希望,人会不会因此陷入虚无呢?在1961年的一次讲座中,有人问海德格尔:“如何认识存在呢?”他的回答很简单,“花更多的时间待在坟地里。”海德格尔认为,恰恰是因为“此在”有死亡,所以意义问题才会出现。因为此在是极为脆弱的,所以如何做出选择、如何审慎地对待生活就显得格外重要。换句话说,人们越是清楚地意识到虚无的可能性,越会导向自己本真的存在。所谓“向死而生”,只有无限接近死亡,才能深切体会生的意义。当我迷茫“躺”下的时候,海德格尔轻轻的拍起了我的肩膀,告诉我,“伙计,你不能这样躺着,你要呼唤自己的名字!唤起自己的良知!你的未来有许多可能性会发生,你要在生命终结前,去行动吧!去成为想象中的那个可能存在的能在(自己)!”
